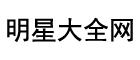《红房子》第二十四章
大年三十的晚上,飘起了白花花的雪。不知道为啥,一个冬天里,天上要是没有落下几场雪来,人就总感觉不是个真正的冬天,年也过得没滋没味。那晚的雪,是母亲先发现的。她在灶房忙活,去外面抱柴火的时候,感觉到了。她过来给我一说,我急忙从房子跑出来,站在院里朝天上看,又拿手在空里去托。手上没有,但脸上的汗毛一动,麻酥酥地痒,我就知道是比盐大不了多少的小颗粒落下来了。再就变大,像天上有人抓了一把肥料往下洒,肥料是复合肥,颗粒比芝麻大。这时候母亲就嚷着要往柴火上盖塑料纸,不盖的话,柴火湿了就得好多天晒。塑料纸盖起来,就能听见雪落在上面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溅到地上,蹦蹦跳跳地往前滚。后来竟如搓棉扯絮一般,打着旋儿,在空里洋洋洒洒地往下飘。飘下来就落住,再不化,一层叠了一层。脚踏上去,就有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了。
下午我拿了根竹竿,顶上绑个笤帚,把墙上的灰和蜘蛛网扫了,就剩下擦洗门窗。母亲在灶房里炸油锅,火烧得旺,油就在锅里滚,“啪啪”地往墙上溅。她一点儿也不惧,手里的漏勺在锅里上下翻飞,锅台上的盆里黄亮亮的豆腐和红薯就垒成了山。她每新炸出一锅来,就要让我吃,说:来,尝一下,看这是焦了还是嫩了。我在干活,手脏着,但不愿意拂了她的兴,就过去张着嘴,嘻嘻笑着。她将东西拿到手里,都要给我喂了,却害怕烫,在自己嘴边吹了吹。我吃到嘴里,故意用舌头搅,腮帮子一鼓一鼓,像没牙的老婆吃东西一样,说:哎呀,烧很,烧很。她紧张了,说:快吐了,快吐了,我都吹了的呀。我“哈哈哈”地笑起来,她也笑起来,把手里的漏勺举成了打人的姿势,骂道:咋恁瞎的,再不给你吃了!我装着害怕的样子,避得远远的,说:炸的这啥么,苦!脸上做出难受的表情,眉头皱着。她说:那你过年就把嘴封住。我手朝锅里一指,说:看,焦啦!她脸上失了色,低头去看,我猛得伸出胳膊,装着要去盆里抓,她意识到,漏勺又抡起来,说:打!我就跑开了。
与母亲一说笑,我心情就有些好,挽了袖子准备去擦洗门窗。我端了一盆水,从灶房门口过,她看的是锅,眼睛却立即翻上来,说:你盆里端的是热水还是凉水?我知道她的心思,偏说:热水。她说:我就没有见你到灶房来么,你端的是热水?我说:我从炉子上倒的。炉子在堂屋里,上面坐了个水壶。她说:你来让我试一下。我说:你那手有毛病哩,敢试我这水?我这水兑得冰。说着偏走过去,把盆子端到她面前。我哪里想到她真的就伸了手,入了水,触电般得缩回去,骂道:狗日的,天冷得跟啥一样,你就给我动凉水,看你到了我这年龄咋办呀!你要是不听话,就把盆放下,等会闲了我抹洗。我知道她就没有闲的时候,便真的去兑了热水,她才笑逐颜开了。
收拾完了我去陪母亲说话,顺便烧火。她在岸上擀面,脚底下垫了两块砖,垫得高了好使劲。擀薄了摊开,切成一节一节的碎片,碎片都是一根指头那么长的菱形。两手掬了,撒到油锅里,开花一样,面片的肚子就鼓起来。我稀奇得看着,母亲说:离远些,小心油蹦,溅到你身上。我笑着,说:妈,你这手艺都是咋学的?她手里的漏勺停住了,看着我说:当然是跟你奶学的么。话才说完,眼睛就红起来,眼里也有了快要噙不住泪水。我没有说话,低着头往炉膛里添柴,她极快地用手背把眼睛抹了,说:你奶睡到那儿,啥都不知道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只是一个劲地添柴。母亲说:好了,不用添柴了,火不要太焦。又说:你去看你爷把对联写好了么。年年都写哩,现在是越写越慢了,老了老了心性还恁强的。去,赶紧看去,好了就赶紧贴上,不要啥事情都干到人后头。我应声去了,我不愿意让母亲觉得我好像不难过,我其实只是一时眼泪流不出来。
祖父手里捏了只笔在纸上写,老花镜已经掉得挂在鼻尖上,纸上的字写得有毛栗子那么大。他看我进来,说:得是你妈让你过来催我哩?我说:没有,我闲着哩,过来观摩一下。他说:你去把毛笔,墨水,纸拿过来,我这再剩一句了。人一上年龄,脑子就不够用,半天写不出个名堂。我挑了门帘到房子去取,他又喊道:倒些热水把毛笔泡一下,软了好下笔。我说:啊。等我把东西取过来,祖父却已经写好了。他朝我招手,说:来来来,你过来看一下,我写了四幅,一幅短的贴前门,剩下长的你挑一个贴二门子。我看了写的是:
逢佳节思亲,至老来念旧。
迎新春旧事少来讨扰,辞旧岁新人多时呈祥。
勤俭持家不忘祖辈恩德,安宁度日休提邻里仇怨。
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独吞许多愁苦,地上刨锅上转多少载只为子女成人。
你看出来了吧,这四副对联,联联都没有少了祖母。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此地有情义,这我没有见过。不用嘴去说,只用心去想,才当得起情义二字吧,我反正这么觉得。祖父问:没有错别字吧。我说:没有。把纸叠了要裁。纸是蓝纸,我们那边讲究亲人不在世未满三年,对联是要用蓝纸写的。他又问:选的哪两副?我说:最长的跟最短的。裁我的纸不看他。他说:为啥不选那两副?我说:我是看哪个顺口了就选哪个。他当下有些变脸,说:你书都念到哪儿去啦?一点文化都没有!我“嘿嘿”地笑了笑,只是裁自己的纸,有文化没文化我自己当然知道,关键是我不能让他把我的心思看破。祖父手还是背着,肩膀往上晃了晃,披着的大衣便回正了,说:纸裁好了叫我!出了堂屋门,走到院里去了。
把对联贴上,天就黑得看不见人影了。
晚上八点准时,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没开始之前,我已经给母亲打过预防针,说年年她都是在锅上忙,今年无论如何要一起看电视,她连我看都不看,嘴里只是应承着。我到灶房去叫她,她正把裹了面的带鱼往油锅里放。我说:走,妈,晚会开了,美的很。她看我一眼,说:我不去,那有啥看的,过来过去都是光胳膊光腿的人在台上蹦哒,哇啦哇啦也听不清唱的是啥。我说:走嘛,一起看热闹。走!她说:热闹啥哩,你跟你爷看去,我不顾锅上,人家客来了干瞪眼呀!我拿了锅盖要盖她的锅,说:你咋说话不算数哩?她当下翻了脸,把我手里的锅盖抢过去,说:去去去,再不要给我捣乱,一条带鱼几十块钱哩!
看了一会,母亲端着盘子进来,房间里立时香起来。我说:咦,你不是不来么。母亲把筷子给祖父手里递,说:你当我来看电视呀,我让你爷尝一下这鱼炸得嫩还是老。我说:不让我尝呀!母亲说:谁叫你淡话恁多,要吃朝锅上走,还让我给你端过来呀。我哈哈地笑,把她手里的另一双筷子抢了过来。我夹了鱼,母亲的眼睛始终跟着我的筷子走,看着我吃了,问:咋样?好着么?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说:你不知道呀?她说:这娃,你嘴里吃着哩,我咋知道?我说:你没吃吗?她愣了一下,说:哦,一出锅我就尝啦。我眼睛盯着她,说:真的吃啦?她不看我,去接祖父手里的筷子,说:吃了就是吃了么,还有真的假的呀?我把筷子放在盘子里,她说:还有一疙瘩哩,咋就把筷子放了?我说:我吃好啦。她说:都端来了还让我端回去啊。我说:我嫌吃着麻烦,还得挑刺。她说:带鱼这刺也叫刺啊?说着又要让我吃,祖父眼睛瞪了瞪,她端着盘子回去了。
正看到主持人报幕说,下一个节目是秦腔选段,祖父便叫我:去,叫你妈去。我走到灶房门口,门闭着,里面是油滚的声音。我用指甲在门上轻轻挠了两下,学着猫叫“喵”。门里没有反应。我又挠了挠,叫了两声,一高一低。母亲听见了,说:这谁家这猫。我偷偷笑了笑,本来想把母亲引出来,又害怕把她吓一跳,就推了门进去,说:赶紧,妈,唱秦腔哩!母亲的手就停了,抬头问我说:哪一段?我说:周仁回府。她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出走。走出去了,喊着说:把盆里的东西拿锅盖盖上,门闭严,我刚听见谁家的猫在院里踅摸哩。我又偷着笑了笑,临盖锅盖了,捏了一把油炸花生米吃了。
唱腔一起,祖父和母亲就来了精神。母亲说:快给我取眼镜去。我起身就听见了戏词:一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恨严贼逞淫威一手遮天,背地里把圣上一声瞒怨,宠奸贼害忠良不辨愚贤,老爹爹禀忠心反遭刑贬,年迈人怎经得牢狱熬煎。祖父闭着眼,跟着曲子摇头,手在床头上“梆梆”地打着拍子。我说:爷,你咋不看哩?他说:不要言传!等一曲终了,他说:听秦腔听的就是调调,眼睛不由得就闭上了,你们碎娃不懂!我悄悄问母亲:妈,那你咋看哩?母亲说:看人家这演员长得好看么。你说人家咋恁会演的,说哭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
母亲再到房子来的时候,又端了一碟虾片让我和祖父尝。她一进来就说:外面下雪了。
我立即站起来,说:真的?不等她回答,就跑了出去。听见她说:一口不吃就跑呀?跑得急,黑暗里凳子腿把我绊了一下,我本来不想扶,想着母亲出来的时候也被绊了,就朝里挪了挪。开了堂屋门,就有一阵风迎面而来,凉嗖嗖得缠住了身子。有一片雪就飞到了我的睫毛上,痒痒的,我眼睛眨了眨,它落了。我转身回了房子,也不开灯,从书包里把烟摸出来,就上了楼。
我偷着在房上抽烟,被母亲发现过几回,她就不允许我轻易上楼了。但下雪了就可以光明正大地上去。我上楼吧,也不光是为了抽烟,在楼上能看见我的祖母。这话我给你说了,你要保证给我保密。祖母现在在地里睡着,她盖的被子是一疙瘩隆起来的土,被面是长出来的草和开出来的花。野地里没有墙挡树遮,风自然就大,下了雪,她就能多盖一层。我每次上了楼,都是站在西北角,面朝西北,远远地望着,我知道我站的地方离祖母最近。白天里,能看见三颗大柳树。柳树是上坟时插的,但柳枝见水就活,几经砍伐,仍是旺盛着,且越发粗壮。我就是靠那几颗柳树辩的方位。柳树谦卑,树叶子永远都是低低地垂着,从不张扬,这样的树陪在祖母身边,我感到很欣慰。每一次到楼上,我都是轻手轻脚地走,我宁愿让母亲以为我是偷偷地抽烟,至于我的其他目的,我不愿意让她知道。她本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只要一提到祖母,她立即便能落下眼泪来。她每次洗锅,常常是一边洗,一边痴痴地说:‘乏了就歇着,把锅撂下,我明天起来早些洗’我现在再都听不见这句话了!我不像她,我不会把那些东西表现出来,只是偶尔,在没有人的夜里,悄悄哭一回。我的哭,谁都没有见过。
初一早上照例是响了鞭炮,吃过七碟八碗,就闲下来没有事干。上午给祖父捏肩捶背,下午去村口凑了一会敲锣打鼓的热闹,天就黑下来,看不清了人的高矮胖瘦。初二自然是待客,客人一杂,手稠眼多,有人带来的小娃就把喜欢的东西往自己口袋里装。我端着盘子去房间倒瓜子花生,出来放到桌子上,站到一边听大人说话。母亲起身,说:这娃,把盘子往满地倒么。端着盘子又进了房子,出来时把门使劲拉了一下。我看盘子也并没有添多少。母亲用眼色把我使到了灶房,悄声说:门把你尾巴夹住了?人这么多,留着门进贼呀!
忙活了一天就累,迎来送往的,光是点头哈腰就有说不清的次数。晚上倒头就睡。我只说年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初三下午童曼瑶却进了我家的门。
那时候我在房子看电视,听见门环响了。母亲大概是从灶房走出来,说:欸,这谁家的娃,是不是头一回走亲戚,没有到我村来过?童曼瑶却开口叫了声“阿姨”,笑得虎牙就露出来。我听见了声音,但我绝没有想到是她,就没当一回事。但我明明听到她说:我找皓子哩。母亲就扬了脖子朝堂屋喊:皓子,你同学来找你来了!
我真以为我的同学来找我了,出了房子才看见童曼瑶花枝招展地提了大包小包,我就愣住了。过去把她手里的东西接住,说:你咋知道我屋在哪?她说: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不会问人啊。得意的朝我挤眼。我说:你胆子大的很,一个人跑恁远的路,推门你就进来,你不害怕我屋有狗啊。她说:我当然先敲门嘛,没有动静,我就进来了。
母亲听出来话的意思,过来掺和。她端了杯茶递给童曼瑶,说:快坐快坐,哪个村子的啊,娃?童曼瑶接了水,说:哦,我屋在西安哩,阿姨。母亲就明白了些,说:噢噢,不是他同学啊。拿眼睛看我,我只好说:啊,我单位同事。没想到童曼瑶尖声说道:我是她女朋友。母亲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一拍大腿,说:哎呀,好好好,欢迎欢迎。皓子你还立着干啥哩,快去把瓜子花生端出来,盘子装满,还有糖,要好糖!然后她回头对童曼瑶说:你先坐着啊,叫我给你做饭去。要是坐乏了,就到炕上睡一会!高兴地去了灶房,走路都不稳了。
我拿眼睛瞪童曼瑶,她朝我嬉皮笑脸。这时祖父掀了门帘从房子出来,童曼瑶站起来问候,说:爷爷。祖父说:哦,好,来了啊,坐坐坐。扭头对我说:皓子你把人家招待好啊。我点头,说:啊。祖父就到灶房给母亲烧火去了。
童曼瑶不知道拘束,跟我坐了一会就嚷着要去灶房帮忙。我说:你勾子底下有虫啊,坐着,不要到灶房去。她撅起了嘴,说:咋了嘛,我去给阿姨搭把手。我说:我爷在灶房哩,你不要过去给我胡成精。她就吐了舌头,说:你爷看着威严的很,手一背看起来像毛主席。我听了就笑,说:你知道就好,我爷在屋里咳嗽一声,我跟我妈都打哆嗦哩。她悄悄地说:是吗?装着很害怕的样子,故意打了个哆嗦。我就在她屁股上打了一下。
吃完饭天黑以后,我就带着童曼瑶在村里转。她要拉我的手,我抖开了,说:这是农村,不是城里,人都眼尖得很,你注意点!她的嘴就撅起来。撅过了,仍旧是欢欢喜喜地跟着我。到了北巷,我给她指,说:看,这是北巷,我老屋以前就在这个巷道子里。那个时候住的还是木架房,我就是在这边被我奶一手抓扒大的。童曼瑶看着深不见底的巷道,有些害怕,躲到我后面说:你奶功劳大啊。我说:我奶一天福都没有享!到了南巷,我还给她指,说:这是南巷,南巷东头新置了一院庄子,以后咱俩就住那。她说:咱还住农村啊,你会种地吗?我说:废话,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不会种地?
回到家里,把童曼瑶安顿到房子,我出来到门外头的茅坑上厕所,听见母亲和祖父在房子说话。祖父问母亲:这娃晚上不走啊?母亲说:走哪去啊,远的跟啥一样,娃人家她屋在西安哩!祖父说:不走往哪住哩?母亲说:人家娃跟我能睡么,炕那么大哩。都走出来了,又转头对祖父说:你睡你的,再不要操心这些事,我一会给你把尿盆提进来。祖父说:不要让那两个睡一块啊!母亲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你看电视,我走呀。出来闭了门,把窗帘也放下了。
母亲一转身,看我在堂屋站着,我俩眼神一对,她就悄悄地笑起来,小声问我:听见了?我说:听见了。我俩又笑了一回。她问:你俩咋安排哩?我说:那就跟你睡吧?母亲挤着眼说:当真?我咋都行,要看人家娃愿不愿意哩。我说:那叫我去问一下。母亲在我腰上戳了一下,说:装。我就“嘿嘿嘿”地笑起来,朝房子示意了一下,说:那我睡呀。她说:睡去,睡去。我就朝外走,母亲说:干啥呀?我说:上个厕所,顺便给我爷提尿壶。母亲说:你上你的,尿壶我提。我说:我一捎就行了,你不来了。母亲瞪了我一眼,说:你到人家房子是寻着挨骂呀。我“哦”了一声,母亲又走过来,把我拉住,说:等你爷睡了你再睡。我答应了,她又说:我给你抱两床新被子。说完到立柜里翻腾去了。
那天晚上,我确实是等祖父睡下,才关了门,把门闩闩上,用铁锹在后面顶住,用木板把门下沿封了,才上的床。
《红房子》第十六章
童曼瑶自从睡了一回红房子,晚上就很少到宿舍去了,她说她早都反感了宿舍的人到了半夜还叽叽喳喳。她说的是废话,那些人能跟我比吗?刚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跟我一块回,总是吃过饭自己先到宿舍里打个转,天黑得差不多了,她就往过走。但天一黑,红房子里的灯光就幽幽地,树再一遮,便黑白相对地显出些阴森来。我是经常那样走,习惯了,越是害怕,就越光明正大地走。但走上去了,还是要把门上反锁的那个疙瘩按下去。童曼瑶毕竟是女人,头一晚上过来,离得老远,就叫我的名字。按说为了避人耳目,她是不会大声叫我的。我明白她的意思,本来想开个窗户答应她,但还是立即下了楼。再后来,我给她交代地很清楚,只要她准备出宿舍门,就给我发个短信。
一立秋,晚上在房子要是光着脊背,窗户关了,房子门闭上,还是觉得有风。风像水一样,是无孔不入的。但我愿意撑着,总觉得身上穿的少了,胳膊才是胳膊,腿才是腿,干啥都方便。这期间我回了一趟家,为的是把地里的苞谷掰回到院里去。苞谷熟得过了,有的已经吊在苞谷杆上。架子车往回拉,母亲说装得少了轻快,不挣人,但我不愿意。我心里想的是少拉一车是一车,少跑一趟是一趟。装满了,还要拣缝隙把苞谷棒子一根一根地往进插,就把架子车插成了刺猬,圆圆的脊背,胖胖的肚子。倒了几车,院里就有了山,山是黄的,山上的石头禁不住坡陡身圆,有的就骨碌骨碌地往下滚。山脚下,有一条一条的虫爬出来,都吃得胖得像蚕。天气预报虽然报的是晴,但害怕变天,就连夜把皮剥了。剥了皮接下来就是脱粒,你知道那时候是咋样脱粒不?你见过专门用来脱粒的那个锥子么?筷子粗细,一乍长短,往往是把上会弯一个圈,套上个苞谷芯子,在苞谷棒子上戳,一锥子下去,苞谷就少了一行。然后就是用手剥,但苞谷颗面虽然光,却硬得像石子,坐到那腿还没有麻,指头蛋就磨得粉红,第二天连馍都抓不到手里。脱粒虽然是个慢工活,但我还是等全都剥完,把苞谷颗一袋一袋地背到楼上去,才回到了单位。我不等能行吗?几千斤的苞谷,我不背,母亲养这么大个小伙子干啥呀?
要是天好,在房顶上再摊得薄薄得,也就是两天半,苞谷颗拿到手里就掐不动了,这时候才能变成钱。我的假虽然不长,但我愿意迟回去几天,大不了扣我的工资。我哄母亲说我给领导说了,没有说死,只说活干得差不多了就回去。但母亲不,她一个劲地说不能把单位的事情耽搁了。后来回到单位,只要出门,我就时不时地看天。对它说:你好好的,你不敢阴,要晴,晴得亮亮得,越亮越好!老天爷估计也是知道下苦人不容易,在我走了的一个礼拜,都让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念了它的好,背地里看了好几回它,一回朝它使劲点头,一回对它流了眼泪,还有一回,我把眼睛闭上,想象着自己给它跪下,磕了个头。它虽然把我们照顾了,我感激它,但我宁愿母亲不再靠它吃饭。这些事我没有给别人说过,我既然敢给你说,我也不嫌丢人,丢人算啥嘛,人只要好好地活着,有机会干自己想干的事,比啥都强。
在城里呆的时间一长,我也成了细皮嫩肉的人,但我不喜欢这样,总觉得中指和无名指根底下,有两疙瘩颜色深一点的死肉,手上才算有劲。农民的儿子,除了身上有劲,还有啥能拿得出手呢?回去干了几天活,我指甲缝就有了许多肉签。肉签你知道吧?就是你用指甲掐不住,有的甚至看不见,但你把胳膊往衣服袖子里面穿的时候,就能觉得指头像有针在扎一样。那一个晚上,童曼瑶压住我,把房子所有的灯都打开,用指甲刀齐齐把我十个指头寻了一遍。她住到红房子以后,今天给我煮个鸡蛋,明天给我熬个稀饭,我自己头发梳得光了,衣服也换得勤了。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原来有了媳妇,才算是上流社会的人,她只是偷偷地笑。早上出门,她给我把领带打好,套到脖子上。套上了还要围着我转一圈,看衣服领子有没有翻好,再拍一拍我肩上的头皮屑。我这人讲究,经常要看一下领带的长短,这时候她就要打我捏领带的手,说她都是提前量了的话。我就笑一笑,再不管。但是出了红房子,我还是要看一下。看完了就把头抬起来看窗户,窗户里是她嘴里咬着皮筋在扎头发。
童曼瑶人虽然睡在了红房子,但她早上从来都没有跟我厮跟着出过门。有时我走得急忘了烟或者打火机,她就把窗户打开,把烟攥在手里,胳膊伸得高高地摇,很得意,就好像是抢啥东西抢到了一样。我手把她指一下要返身,她就趴在窗户上喊:你先去,我一会给你捎过来!我给她说过,我说事情已经都明成镜子了,何必哩!他谁还不都是从这一步过来的!她说你是男人你无所谓,我是女人我总要给自己留些脸面,再说我将来还要嫁人哩!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年轻人谈的恋爱,好像真的是浮躁地根本想不到婚姻,只是两个人相好而已。但其实童曼瑶她只是嘴上的功夫,她年底就跟我说起了结婚的事。
天明了,一睁眼,照旧还是上班。进了侧门,脚自己就知道朝湖西楼走,我不用指挥它。前面两个保洁阿姨抬了一筐子树叶,一走一晃荡,就有叶子从框里洒下来。我跟在后面拾了,撂到垃圾箱里。我一般手洗干净了,就不爱摸啥脏东西,但我知道阿姨的工作不容易,我无非是再洗个手的事情,没有啥。再有就是,我看见她们粗糙的像树股一样的手指头,脸上稀松地像没有血肉的皮,我总是想起我的母亲。母亲和她们一样,扫院里的树叶的时候,偏偏不用簸箕,用手就把树叶揽到了笼里。我说她咋干啥都是用手,她只是笑,笑着把手藏起来,害怕我看见她早已经洗不干净的指甲缝。指甲花你见过么?花开了以后,摘了,捣碎,敷在指甲盖上,然后包住,一个晚上就有效果。但要是染得不好了,色上得不匀,整个指头蛋都是酱色。母亲的手指头就是那个样子。我正想着,就听见两个阿姨说话。一个说:哎呀,到了这季节,光是树叶子都叫人一天闲不下来。另一个说:唉,可不就是,一个月也就挣几百个元,领导还嫌这嫌那的。一个立即就接上了话,声音高了说:再不要提领导,领导一天光动嘴不干活,把咱使唤地一个劲。另一个说:混一天是一天,快的很,眼看就到腊月了!
到了办公室,我一推门,看见王爱云正吃早点。这女人总是比我来得早,来得早了又总是在办公室吃早点。常常是我进来,房子里一股油香味。这其实没有啥好说的,我要说的是我。我的原则是要么不吃,要么吃了再来,总觉得办公室不是吃饭的地方。王爱云背对着门,门一开,她脖子动了一下,似乎是噎住了。赶紧朝后看,一看是我,放了心,笑一下。我说:早,云姐。她一边说“早”,一边用手把嘴挡住,害怕吃的漏出来一样,又用手指了指桌上的盘子。我会了意,点点头,但没有动手,拿起桌上的杯子,拧紧盖子摇了摇,把陈茶倒了接水。她就不再让我,只顾吃。我给你明说,她让我我也不吃,我就是试她哩!要是我,我让人会把东西拿到手里递过去!谁不接,我都能跟谁翻了脸!但我不会跟王爱云计较,她几十岁了才跟我混的一个样子,我以后的路还长着哩!
王爱云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嘴就空了,说:皓子呀,看你这一向红光满面的,是爱情把娃滋润得?我笑着说:啥爱情不爱情的,我们这是碎娃,耍哩。王爱云挤眉弄眼,说:早上瑶瑶从红房子出来,跟个贼娃子一样,你当我没看见?我脸就红了,说:哎呀,好我的姐哩,咋成了贼娃子了。王爱云哈哈地笑,笑完了,说:晚上替姐值个班,姐有事哩。我说:行嘛!把柄在姐的手里握着哩,姐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邪门的很,晚上就出了个事。到现在我还在想,为啥怪事情都能叫我碰上呢?
晚上一般没有啥事,说是值班,领导都走了,也就放了羊,我有时在湖西楼看电视,有时到院子转一转。到了院子,休息室要是没人,再看哪个客房的窗户幽幽地闪着光,我就知道服务员也看电视哩。客房住人不住人,我心里当然有数嘛。一般我不太管,都是人,谁还不想利用个职务之便?只要工作干到位了,其他的,都好说。但这时候我就悄悄地走到房间门口,装着喉咙里有痰,“嗯”地一声,房间的光马上就灭了,然后就是一片安静,砖头底下还是墙缝里的虫,叫唤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我说:开门。房间的门就开了,服务员出来朝我嘿嘿地笑。我看着服务员,故意把眼睛瞪着,她们还是笑。我说:咋弄?交罚款还是写检查呀?服务员就紧张了,头低下去。这时候我就笑出声,把食指弯成钩,刮服务员的鼻子,说:注意点啊,别让转着的领导看见了。
我走了,关系好的就在后面喊:皓子,辛苦啦!我还没有出院子门,就听见服务员又进了房子,把门闭上了。
一天到晚都是那些事,过来过去就没有了意思。从院子出来朝回走,我心里说还是到湖西楼看电视吧,看电视不费脑子,时间就过得快。迎面却走过来一个人,步子走得晃荡,头重脚轻,像踩着高跷。胳膊一甩一甩地,手里又好像提着个东西,定睛时发现是酒瓶。知道是客人醉了酒,就想着是不是给扶到客房里去。才说要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这人的胳膊却猛得一举,手里的瓶子“当啷”一声摔到了地上!这一下我虽然料想到了,但没想到他真敢摔!黑漆半夜地,本来就静,这一声脆得简直要把我的耳朵扎烂了!当下站住脚,心里烧起了一团火。我生平最逊耍酒疯的人,你到了你屋,你哪怕把锅砸了,把床揭了,把柜掀倒,与我屁不相干!你当着我的面,当啷一声,你想干啥?给我示威哩?更何况这是公众场合,更何况这地方还是我管着!都说要扑过去把那人放倒呀,却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就骂自己:你干啥呀?!人家是客人,掏了钱人家就是尊贵!人家就是把酒瓶子摔到你脚底下你也不能吱声!不要啥事情都是动手,你是人,不是畜生!牛在一块是顶,鸡在一块是啄,狗在一块是咬!有些人你不能跟他计较,你计较了,也就跟他一样没文化。这道理我懂,但我要叫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就点了根烟,头仰着朝前走。走到跟前,眼睛把他瞪了一下。走过去了,我听见他把玻璃渣子踢了一脚。我心里冷笑了一声,走到湖西楼门口,并没有进,一闪身到了暗处的树底下,看他进了院子。
现在我想起来,觉得还是多亏自己留了个心眼,不然我一时扑不到院子里去,耽误上一半分钟,就有可能出更大的事情。接着说吧。我坐到办公室后,开了电视,心就慌得有些看不进去。这我一点儿都没有给你夸张。我虽然不是个能料事的人,但遇见事了总是爱朝瞎处想,遥控器拿到手里换台,上一个台还没有出来,就着急按下一个台。按得快了,台一下就跳了三四个。知道再坐不住,就心里说还是到院子去转,全当是巡逻哩。指望那些保安?这会说不定在那抽烟打牌哩!出了办公室,正反锁门,座机便响起来!响起来我倒没有多想,因为有时半夜了,经常是童曼瑶不打我的手机,捏着鼻子在座机里装领导。我抓起电话,还没有“喂”,就听见里面有女人“啊”“啊”地叫声,声音远远地,就像是开着免提,离老远喊一样。声音远了就弱,再加上有杂音,我听不来是啥情况,就以为是谁打错了,准备挂。这时候话筒里“咚”地一声,像是对方的电话摔到了地上,又有电话在地上拖动的声音,“次啦”“次啦”地响。我耳朵被震了一下,立即警觉起来,把话筒鼓劲压到耳朵上,想听清里面的声音。果不其然,里面就有了女人微弱的声音,像是在与啥东西做着抵抗,身上已经没有了劲,但还是挣着挣着喊:主管......主,主管......我立即回道:咋了?咋了!声音大得感觉能把自己的头皮顶破。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了哭喊声:救命,救命......
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我知道女人能吱哩哇啦地喊救命,那肯定是碰上瞎人了。女人天生不是男人的对手,更何况是瞎男人!我放下电话就往出跑,越跑越觉得身上劲越大,血流得快得要把血管都挣破了,而拳头也攥成了个铁疙瘩。但跑出去了才想起来没有问是哪个院子,哪个服务员。这时候那个醉了酒的男人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是他还能有谁嘛!才跑到院子门口,就听见服务员的叫喊声。我说话你不要嫌难听,但叫喊声真的撕心裂肺地像杀猪。院门开着,我扑进去,猛得一黑,我心里就紧张起来。我这么说你不要笑话,谁就是胆子再正,也顶不住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但这时候还能顾得了那么多?休息室里面灯亮着,光从里面透出来,在地上照了个方格。叫喊声一直在持续着,里面也就有了男人的声音,就像是猪吃食一样的那种“哼哼”,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突然我就觉得个子高了,一步跨到门口,推门门却没有动,里面被闩住了。我心里说狗日的恁着急的,都知道锁门,脑子还是清醒!手就举起来,一掌一掌拍到门上,叫服务员的名字。服务员的声音高得竟像是我在千里之外一样,粗得又像是要把喉咙挣破一样,喊道:主管,主管......接着又骂道:滚,你给我滚!我知道她是在骂那个男人,往后一退,一个垫步,右腿就弹出去了,我觉得我的腿像打仗时攻城的木桩子。门“哐当”一声开了,我就看见那个男人把服务员压在休息室的床上。服务员挣扎着把男人往外推,表情难过地像是在生娃。衣服已经被扯开了,半个肩膀露出来,肩膀上有一条黑色的内衣肩带。脚上的鞋已经掉了,脚在空里乱蹬。男人爬在服务员身上,一只脚在地上撑着,一直腿已经上了床,打着弯搭在服务员腰上。我当时就震惊了,心里说:狗日的,老子都进来了你还敢胡来!服务员看见我进来,眼泪哗啦啦就流出来。我已经等不及她喊,扑上去,两只手像铁钩子一样“啪”地一声吸在了男人的肩膀上,猛得一提,左手一推,右手一拉,就让这男人转了个身。转过来我就恶心,他嘴里的哈喇子溢出来在嘴上抹得匀匀的,被光一照,亮得像抹了猪油。我一拳打到他脸上,他往后退着就瘫到了后面桌子上。
吴萍在床上躺着,头发已经乱得遮住了脸,但没有遮住她眼里的惊恐。她衣服的一角已经被掀起来,肚脐眼像一颗眼睛一样睁着。我给她伸了个胳膊,她手都抬起来了,却只是指头把我手挨着,拉不住。我一下子握住她的手腕,猛一鼓劲,把她拉到了我脊背后面。她已经站不稳,两手搭在我肩膀上,我对她说:把衣服穿好。把她的胳膊放在了门把手上。虽然我知道她身上没有了劲,得要人扶,但我现在要腾出手来对付那个男人。我说:衣服穿好了往出走。说完我扭了头,眼睛死死地把那男人盯住,他额头就渗出了汗。他挣扎着往起站,眼里放着凶光,说:你谁呀,狗日的!我说:我是你爷!一脚踏到他肚子上,他还没有起来又坐倒了,靠在桌子上,头歪着,像一滩泥。我转过头,看服务员已经能站住,问她:你身上有劲么?她愣了愣。我走到男人跟前,不放心,朝着肚子又踏了一脚,他“哼”了一声,几乎钻到了桌子底下。我把他扶起来,站到他背后,把他两只胳膊背到后面扭住,就像押着个囚犯一样,对服务员说:来,过来,朝这狗日的脸上扇!服务员还是愣着,头发湿湿地粘在脸上,摇了摇头,把身上的衣服紧了紧。我喊道:过来,扇你的,有我哩!服务员还是不过来。我就灰了心,一下把男人甩到墙上,他的头在墙上磕得“咚”得一下。我蹴下去,眼睛离那男人的头有一乍的距离,声音平平地说:以后再不要干这样的事,记住了么?男人没有说话,眼睛还把我瞪着,我直接就是一巴掌,扇得他躺到了地上,吼道:记住了么!?我一吼,余光里看见服务员身子抖了一下。她把我叫了一声,说:皓子。我没有应她,站起来把西服脱了,披到她身上,扶着出了院子。
到了湖西楼,把服务员安顿着坐下,给她倒了一杯热水,递到手里。我知道这事情也不方便问,当然也就没有开口。服务员接了杯子,两只手端着,也不喝,只是头一点一点地抽泣。我是个笨人,最见不得女人哭,也最不会劝女人,我说:好了,事都过去了,不要哭了。服务员的头就点得更快了,一时就有了哭声。再就“哼哧哼哧”地像是快断了气,腔子上湿了一片。我给她递了一截卫生纸,她接了,却越是哭得恓惶。听见哭,我心里就泼烦,想出去吧,服务员又得要人陪着。你有过这样的尴尬么?反正我是觉得,跟男人在一起,能说了就说,说不了就骂,就打。而女人却不行,她只要一哭,我啥都不愿意干,只想把耳朵堵住。我是硬撑着坐在凳子上,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还是止不住服务员的哭,我就有些躁,正准备说“你再哭我就走呀”的话,手机就响起来。我接了,是王爱云,她说:咋回事呀,皓子?话筒里有风声和她粗粗的呼吸声,估计是走得急。我都要说了,觉得毕竟当着服务员的面不合适,就出了湖西楼给王爱云讲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王爱云听我讲完,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信号不好,说:喂?她反应过来,说:皓子,你真打了?我说:啊。她又问:你打得轻还是重?我说:你啥意思?她说:噢......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
王爱云前脚到了办公室,吴雅婷后脚也来了。她俩一来,服务员却不哭了。吴雅婷一进来就问王爱云,说:客人呢?王爱云说:还没有来得及看。吴雅婷说:赶紧打电话呀!派几个娃过去,看人家情况怎么样!王爱云连声应着,把手机往出掏,掏出来却没有捏住,掉在了地上。她急忙捡起来,看了一眼吴雅婷的脸色,把手机拿到嘴跟前吹了一下,打起了电话。电话打完,都要挂了,吴雅婷指了一下,说:让有啥情况了马上汇报!王爱云就重复了一遍。这时候,吴雅婷看了看服务员,问:你不要紧吧?叫了一声服务员的名字。服务员头没有抬,摇了摇,等了一会,说:主管来得及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王爱云用手给服务员把头发拨了拨,吴雅婷说:不要紧就好。那你先回去吧,我们把事情再处理一下。服务员站起来,看了看我,我头轻微地昂了一下,示意她回去。服务员出了门,我们三个都没有说话。我把手机拿出来,给王爱云发了个短信,写的是:你把娃送回去呀!天恁黑的,又才受了惊吓!我短信里给她发的就是感叹号。王爱云看了短信,用眼睛扫了一下我,对吴雅婷试探着问:经理,那我去送一下?吴雅婷点了头。
办公室只剩下我和吴雅婷,我却并不觉得尴尬。我已经记不清我跟她有多长时间没有主动说过话了。她不说,我就不说,我反正无所谓。她把手机拿出来看,我始终没有听见按键的声音。我手里捏了一页花名册,没有翻,只把眼睛留在了纸面上。王爱云回来以后,看我俩都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开口,先是静静坐着,后来就抠起了手上的死肉,抠到痛处,咧起了嘴,吸了一口气。吴雅婷似乎是对这一口气反感了,收了手机,问:客人那边有消息么?王爱云说:还没有。吴雅婷说:小云,你说说,今天这事,咋处理。王爱云手伸到脖子后面挠了挠,楞了楞,说:啊?我说啊?那就,那就按公司规章制度处理嘛。吴雅婷说:你说了等于没说!接着又问我:小张,你觉得咋样处理?我眼皮子往上翻了翻,靠到了椅背上,说:处理嘛,肯定要处理嘛,直接把那个流氓送到派出所就完了么,多省事的。吴雅婷说:我问的是处理咱的人,客人咱能随便处理吗?我说:咱的人?谁呀?服务员还是我?她说:你不觉得你打人不对吗?我听了这话,一句话就不想再跟她多说!
吴雅婷停了一会,说:小张,咱单位是挂牌的四星级酒店,酒店你知道吧,酒店跟旅馆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是星级酒店。人家都说“好事不出门,瞎事传千里”,你这一动手,一传十,十传百,以后谁还敢来咱单位度假?人都有犯迷糊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人家撂倒了,连个机会都不给人家?如果人家是个惹不起,明天酒醒了,叫上一帮子子人来寻事,到时候咋办?我这人脾气不好,是非曲直一定要搞清楚,刚开始我还忍着听吴雅婷说了几句,后来就听不下去了,在她喘气的时候直接开口说:领导,那我问你个事。她明显对我把她说话打断不满,说:你问。我说:那要是你被人在床上压着,你是希望我动手哩,还是光说不练?
宝贝也疯狂的txt全集下载地址
宝贝也疯狂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宝贝也疯狂最新章节TXT----- 《宝贝也疯狂》松柏生著第一册宝贝也疯狂目录第一章天山淫骚震仙魔第二章玄蚌阴功威力强第三章淫夫淫妇配成对第四章国色天香消佳人第五章孝女献身报亲仇第六章巨采夜夜春宵乐第一章天山淫骚震仙魔天山,边缔无际、晶莹的雪峰似擎天玉柱,直插云霄。正值阳春六月,冰雪终年不化的天山山脚。有一片皓大的草原,生机勃勃,万物争奇斗艳。这天,端午节前一天黄昏,草原上传来阵阵似痛非痛。似兴奋的深重的喘息声。只见,草原上有一对男女正在一块铺在草地上的黄布上“翻云覆雨”。这块布里方形,约十丈。宽的十丈,布色黄中带红,仔细一眼,其红色是处女落红染成的朵朵红莲,不下三五百朵之多。只见那压在女子卜面的男子,白发壮男,正凶猛地向身下的女子发起进攻。那女子也似很兴奋一般,强烈地迎接每一击。汗水早已把零乱放在旁边的衣裳弄得斑什多多。白发壮男全身是汗,两眼射光,见天色渐黑,那女子也连连颤抖不已,已至半……
疯狂的宝贝的txt全集下载地址
疯狂的宝贝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疯狂的宝贝作者:延林第一章 出世更新时间2012-12-15 0:31:21 字数:3038 在灵界的南方,有一卵形山脉灵胎山,为灵界三大祖脉之一,灵类聚集之地,自天地初开而诞生至今,乃是一座天地修行至嘉之地,灵胎山上有一门派为太神门,乃是今日灵界三大统御之一,掌管灵界灵山圣地。 灵胎山表面光滑犹如鸡子,浩气盈盈,圣洁之光照耀天地,常常幻化出各类灵兽,宛如仙境,内中自成天地,经过太神门数万载经营,规模庞大,拥有三千灵类聚集,掌门是号称灵界第一智者的玄玉灵尊。 玄玉灵尊在年少时看到一本天地神话奇书,讲述有石猴出世,震惊天地的故事,而后练就一手超凡入圣的点灵之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寻得天地灵胎,点化出一个惊天地的灵物。 于是,在玄玉灵尊刚修炼有成时,点化土灵元胎,得大弟子土元圣,土元圣性格忠厚,虽然是一奇才,但仍不能让玄玉灵尊满意,后在其巅峰时刻,点化火凤石卵,得二弟子火皇圣,火皇圣性格火爆,智慧非凡,但资质平庸,仍不能让玄玉灵尊满意,火皇圣因在门派得罪的人颇多,早在百余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太神门,去了其他地方。 至今日玄玉灵尊六千岁大寿之时,玄玉灵尊要在寿命将尽的时候,将一孕育千年的石胎点化为灵,故而邀来各方好友共同鉴证观礼。 这石胎本是灵胎山内祖脉灵泉中的一颗卵石,因其酷似蛋形,被玄玉灵尊寻来,放置在祖脉源泉之处,受祖脉灵气滋养,玄玉灵尊并为此石胎开启九窍八孔,时至今日……应该是全本了
男主占有欲超强的小说
《娇瘾》百度网盘txt 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E5EVkciRw_P9wmYe7APeA 提取码: zyw4《娇瘾》作者:令栖文案euros珠宝草地晚宴上,沈姒看上了款1830年的“野蔷薇与茉莉花”冠冕。可惜她跟竞价的小明星有过节,不想闹太僵,罢了手。沈姒看着冠冕被送下去,有些遗憾。她正打算起身离场,身侧突然有人坐下来,扣住了她的手腕。现场的声音戛然而止。洋洋得意的小明星把风凉话咽了回去,隔得远,小明星并没认出沈姒身边的男人是谁,但满场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这个人,她惹不起。“喜欢?”齐晟没有理会现场神色各异的众人,懒懒散散地抬眼。沈姒想说不是。但他先发制人,“那就重新拍卖。”
男主占有欲强的小说
1、《娇瘾》简介:京城上流圈人尽皆知,齐家现任掌权人,阴郁寡恩、离经叛道,平素最恨人威胁和掣肘,没养成迁就人的习惯。他仅有的耐心,皆在沈姒一人身上。可惜沈姒“不识相”,得到机会后离开得干干净净。后来,沈姒和齐晟久别重逢,旗袍傍身玲珑窈窕,微微上挑的眼尾稠艳流丹,她盈盈唤了他一声,“三哥。”2、《对你见色起意》简介:燕京附中高二空降两大“魔头”,祖安一姐许昭意,是伪装白莲的翘楚。她顶着一张纯良无害的脸,披着三好学生的身份,脚踩小混混,手撕绿茶。年级大佬梁靖川颜正手狠不好惹,恶劣秉性扬名,飙车打架样样不落,是权贵圈二世祖里的扛把子,结果IMO竞赛横扫考场,空降第一。3、《今天热搜又是我[娱乐圈]》简介:顾娆颜正腿长后台硬,媚骨天成,却放着家产不继承,跑到演艺圈跌爬滚打。某演员:不怕,再不红就改行。顾娆:唉,再不红就回家继承家业。某女星:成名后嫁入豪门,顾娆:嫁什么豪门,我就是豪门。4、《改邪归我》简介:林姣和顾淮之始于一场加了赌注的声色游戏,人皆当顾家这位公子哥秉性恶劣,顽劣放纵,娇养个小情人玩玩而已。谁知几个月后,林姣收了顾母应允的好处,离开得洒脱利落。后来威尼斯水城重逢,林姣想趁着停电逃,却在黑暗中,被他牢牢锁住腕骨。5、《与浪漫热吻》简介:温乔和朋友上选修课,朋友激动地拉着她,“快看!教授笑起来好苏!”心理系的温乔职业病发,“薄唇紧抿,嘴角一侧上翘,眼角无笑意,典型假笑。结合这几节课的观察,我总觉得教授可能是个衣冠禽兽。”她话一说完,正在写字的顾景宸翘着唇角回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