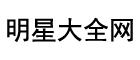求一篇格非《迷舟》的读后感大约在2000到3000字左右
《迷舟》是格非的代表作。格非善于在平实冷静的叙述中剔发命运变幻莫测的微妙精义,使写实的笔触也平添了神秘的恐怖气势。“迷舟”这标题便是人生不可知的主题象征。
大战在即,两军对峙。萧旅长为不祥的预感所缠绕。他原以为灾难将来自恶战,却哪知道阴错阳差中的偶然艳遇竟在冥冥中引导他走向了毁灭——他本是为恋人而去的榆关,却在鬼使神差中与上司的猜疑偶然契合,从而被当作奸细处决……
人生如迷舟。一切的偶然、一切微不足道的琐事乍看起来都平平常常:萧当年在榆关的初恋、后来又投入孙传芳部队中,……可随着命运之神的编织,一切琐事都织成了一张致人死命的网!一切都太巧了:萧为什么偏偏在大战前与杏重逢?萧的对手为什么正好是他的哥哥?一切似乎都纯属偶然。但一切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是某种神秘力量在编排着人的命运。
至于马三大婶是如何进入军事重地、又是如何知道萧与杏的隐秘恋情的?这谜团始终没有解开。作家留下的“空白”又足以引发读者的想象:当故事的结局把萧的迷舟引入深渊时,再回首这个细节,便不由使人对马三大婶、甚至杏的真实身份产生不难理解的怀疑——萧的艳遇是否是一个预先精心设置的圈套?还有一个“空白”:萧追随杏去了榆关,那一夜除了爱的抚慰,还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情没有?萧对自己部队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无意中泄露军机、铸成大错呀……这样的“空白”设置是新潮小说家们的拿手好戏。显然,生活中永远充满着许多是难解之谜、许多无法填充、至多只能猜测的“空白”。新潮小说家有意放弃“全知”的叙述角度,而通过设置“空白”还原生活的神秘面目,同时也为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思考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迷舟》是一部情节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这又是它异于马原等人的“现代派”小说的特色所在。格非本人也写过标准的、寓意晦涩、叙述风格扑朔迷离的“现代派”作品(如有名的《褐色鸟群》便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智慧小说”),但他更擅长写的,还是《迷舟》这样的作品——在写实的风格中通过设置“空白”、通过写人的预感与悲剧的巧合、写偶然中突发的一系列误会改变人的命运、写人心的变幻莫测揭示命运的神秘,进而表达作者对神秘人生的感悟,《大年》、《风琴》、《青黄》、《敌人》等篇都是从这个路子走过来的。这样,格非便似乎具有了双重的身分:既是个写买功力深厚的小说家(他在塑造人物、经营氛围、描摹景物方面毫不逊色于一些优秀的写实小说家)、善于吸引读者的讲故事者,又是个善于超越写实层面、故事层面而升华到对人的命运进行深沉思考的“现代派”。他善于运用隐喻、暗示传神描绘人物感觉的笔法和不动声色、滤去主观情感的叙述风格,也显然得益于“现代派”。这样,评论家们在议论格非时,常常既把他归入“现代派”又把他列入“新写实”的阵营,也就是都说得过去的了。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褐色鸟群的读者评论
《褐色鸟群》注定是一篇你读过就难以忘却的小说,当然不止因为它不好懂。这部小说曾号称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但却很好看。从最外在的方面说,《褐色鸟群》带给我的首先是语言上的快感。“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格非的语言从容而诗意,浸泡着丰富的回忆,勾起人的怀旧情绪。我的周围仿佛弥散升腾起茶色的烟雾,氤氲着歌谣湖畔的水汽。而当这样的语言与这篇小说里扑朔迷离的叙事相遇时,语言就显得格外神秘,扣人心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里的语言是诡异的,当故事还没有展开,当“我”还没有与“棋”相遇之时,语言已经为后面的叙事营造了绝好的氛围。对于一个看似没有逻辑的混乱的故事而言,也许,只有这样诗意而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才能拽着读者,陪文中的“我”走到故事的末尾。而当我们进入到故事本身时,我们发现,世界在被格非一点点颠覆着。小说发表于1988年,而“我”讲述的1992年到“歌谣湖畔”再遇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回忆”,属于未来的时间。小说开头所写的“我”与“棋”的第一次相遇则是比1992年还要靠后的未来。小说的结尾,写到:“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这样时间漫延到了更加不可知的地方。我们的时间被颠覆了,回忆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交错在“我”与“棋”混乱的叙述里,混成一潭。而当故事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是前后两层的,不同的叙述视角在重复中交织着,以《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共同编织成一个故事。令人费解的是,所有我们前面已知的事实,到后面都会被颠覆,最终构成一串类似埃舍尔怪圈的系列圆圈。这一点评家们都有论及,郭宝亮将之比喻为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圆圈概括起来有三重:第一个圆圈,许多年前“我”蛰居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认识多年,我与她讲了一段我与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往事;小说的最后,“我”看到棋又来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二个圆圈,许多年前“我”从城里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来到郊外;许多年之后我又遇见那个女人,她说她从十岁起就没有进过城。第三个圆圈,“我”在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与女人和“我”讲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间构成相似与矛盾。这三个圆圈之间存在相互否定(矛盾)与肯定(相似)的多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这里,一切都难以确定。而故事的细微之处,前后矛盾就更多。比如“我”自称自己蛰居在“水边”,而棋则说“我”是住在“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我”跟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到断桥,看到她从桥上过去,而桥边“提马灯的老头”则否认女人从这桥上经过;更诡异的是,后来这个女人称当时在桥边的是她的丈夫;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丈夫淹死在粪池里,而“我”却看见棺材里男人的尸体似乎动了一下,而且真切地看见,那个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倘若我们可以《罗生门》中不同人的讲述归因于在一个罪案中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那么《褐色鸟群》中不同的叙述则显得荒诞得突兀——我们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动机,到小说的最后,都分不清黑白真假。这样的叙事是完全符合先锋小说的特质的——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去找寻人物内心的奥秘和意识的流动。而格非的这篇小说尤甚。季红真先生认为《褐色鸟群》“由于过于抽象而丧失了叙事的本性,成为一种形式的哲学。”格非的确是在放纵着自己的文字,任它们在存在与虚无的混乱中冲击读者的意识,来完成自己的哲学思考,但是格非并没有忘记叙事的本性,只是《褐色鸟群》中的叙事,遵循了格非设定的哲学逻辑。格非明显受到了萨特等一拨人的影响。按照存在主义,所谓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规定性、个体性、结构性,都是人在与世界接触时主动存在的产物,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映,属于“自为存在”的性质,但这些都不属于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褐色鸟群》的叙事,就是在“自为存在”向“自在存在”的转换中,完成对存在与虚无的终极叩问。陈晓明论述得相当精辟:“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我认为,格非想要描绘的,是他眼中的存在与虚无混杂着的荒诞世间,而他将这世界的荒诞,浓缩在了一个关于“性、梦幻与感觉”这些人类最神秘领域的故事里。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都在质疑着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都在痛恨着这个世界的荒谬,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当我们在格非的故事中完全迷失了支配着的所谓“逻辑”月“定式”,迷失了时间与空间时,我们获得的也许是对这世界最真实的感悟,这就是阅读快感的由来吧,虽变态,但真实。
当代文学起点是什么
先给您格非先生的定义: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 “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 ‘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 “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个人看来,给您三句话,希望对您有启示
一,中国当代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深远,尤其是1978年之后,但是这种影响却是效仿,直接结果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锋小说,马尔克斯句式等等。
二,现代派在中国不可能有,这是西方古典哲学终结的表现,而我们是文革个人崇拜与非理性的结束,两者虽然表象上看都是对于传统的颠覆,但东方并不等于西方,尤其是在哲学上。
三,现代派小说是否真的构成现代派的特质,仍有待分析。